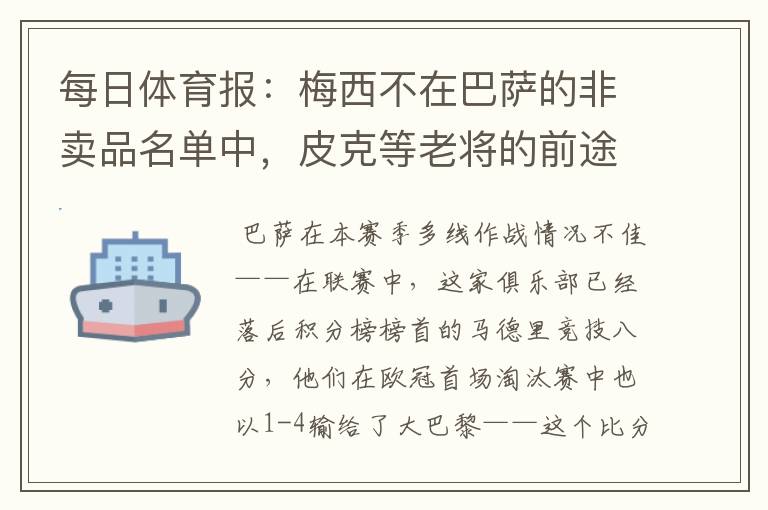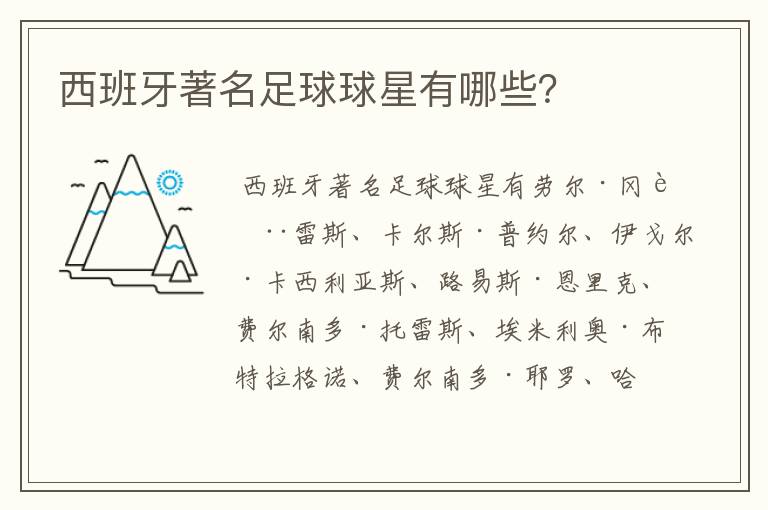﹝擦边球什么意思﹞擦边球什么意思生肖
今天运困体育就给我们广大朋友来聊聊擦边球什么意思,希望能帮助到您找到想要的答案。
- 1、有人见过这么一篇小说
本文目录导航:
有人见过这么一篇小说

答是不是这一篇:
艳遇
要结识一位漂亮姑娘,按书上介绍的,有许多种方法。
比如去图书馆。
馆里照例很冷清。书香味混杂着电加热器的暖烘烘的味道传来。你正在第一排书架上百无聊赖地翻看一本漫画,朱德庸的。这时候你在余光中瞥见了一位打扮入时又端庄大方的姑娘。她刚走进门口,就眼睛一亮。不是因为你,而是因为发现了借阅处桌上的一本书,余秋雨的《千年一叹》。她抓过书切地翻阅了几页。接着,书捧在怀里,她开始转身搜索工作人员。你迟疑了一下,走了过来。自然地,她露出了微笑。你也微笑了。“要看《千年一叹》?”“是呀。”说着她放下书,低头拉开坤包上的拉链,看样子是找借阅证。很快那只纤细又不失肉感的小手就把借阅证拈了出来。这是一张粉红色的过塑的借阅证。学生专用的。然后她等着你的进一步行动。你却讪讪地说,“我不是馆员。我也是来借书的。”她一愣,又有些怀疑地四处打量。你便掏出你的借阅证。这是一张银灰色的过塑的借阅证。市民专用的。“那,馆员呢?”“听旁边报纸阅览室的人说,家里有什么事,一时半会还来不了。”立刻,她露出了焦急的神色。“那怎么办呢?多跑一趟无所谓,书要又被别人借去了呢?上次来问,就说只有一本,被借走了。”“哦,呵呵,就是我借走了。”她这才认真地看了你一眼。你有些兴奋,有些不自在。你灵机一动。“这样吧,我帮你办。”“你会操作那台电脑?”“不,不是那个意思。电脑有密码保护的。我是说我们把书互相交换。我也没事,就在这里等,等馆员回来,说一声就行了。”“哦,对对。那你了。”她去包里拿出她要还的书。拿出来时她还有一点不好意思。你看见了书名,《中国女性的情感和性》,李银河著。你说:“正好我也想看这本书。”她也不搭理你,交换了书,转身欲走。你忙喊住她,“哎,等等。”你说你要抄下她的借阅证号,才好办手续。“哦。我真糊涂。”于是那张粉红色的借阅证再次出现在你面前。你仔细地抄下了借阅证号。看到她的名字,你不禁失笑。“潘婷,呵呵。”“人家本来就叫这个嘛。又不是出了洗发精才改的。”其实你联想到的不是洗发精,而是PANTIE,女内裤。她也不甘心地看了桌上你那张银灰色的,“呵呵,你叫王志文?”在嘻笑中,你还一本正经地问了她的联系电话,说如果办手续有什么麻烦,可以随时联络。
潘婷和王志文的故事就这样拉开了序幕。虚构后面的发展恐怕已超出了我的想象。说实话,我是在很多年以前,读到一位前辈写的在图书馆搞对象的故事,因年代久远,记忆模糊,我复述时只好把背景搬到了二十一世纪。
类似的通过巧遇加上一点心机认识美女的故事很多,当时年轻的我读来也是津津有味。不过后来一概都忘了。大约是它们过于戏剧化和做作,在真实生活中无法模仿。
大学毕业后,我跳了一次槽,工作安定下来,开始物色女友。这时候,我注意到了住在同一栋单身楼的一个姑娘。
她走起路来真叫好看。与竞走运动员有一点相似,只是没有运动员的那种凌厉和蛮劲,而保留了那种朝气和韵律。就象脚底下有弹簧?不过这样说也不妥当,给人轻浮的印象。总之,是不那么张扬的风中扬柳,不那么幼稚的轻盈亮丽。她肩膀平平宽宽的,腰直直细细的,手臂甩得很带劲,头端正不动,而运动发的发端却在随步伐摆动。我就那么注视着她,百看不厌。
我在几次下午上班时发现了她。我慢慢归纳出了她的班次。她是上一天班休息三天。我猜想她是厂电话班的。好象听谁说起过,电话班的女孩工作比较清闲,值一天班就可以休息三天。
这期间厂里办了一个新职工培训班,象我这样调入或分来的大中专生被集中起来进行英语培训。在班上认识了小杨小李小王几个女生。她们都二十左右,学生腔十足,实际上她们是省城某中专的应届毕业生。她们的寝室就在那个女孩的隔壁。
一天傍晚,我把一封从小杨母校来的信带给她。小杨就让我吃她老家的麻糖之类特产。我客气了一回,还是吃了。她们寝室里正好有个青年女工在那里玩。我乘机向她打听隔壁寝室的情况。她说那个胖胖黑黑的叫张小梅,那个白白瘦瘦,走路一阵风似的,是电话班的何艳。她们那一批都是两年前技校毕业分过来的。
我心中暗喜,但也不动声色。为了避免露出什么痕迹,我又转身跟小杨扯到了她的盛产麻糖的故乡。
过了几天,下午下了班,见何艳正在水池那头洗衣服和胶鞋。我回到寝室,换下外衣,梳了一下头,端起脸盆,也去水池边。一到那里就傻了眼,几个洗衣洗菜的占据了她旁边的水笼头。我到水池这一头,闷闷地洗着衣服。过一会儿她旁边那个洗菜的走了,但我也不好意思再凑过去。
吃完晚饭,天快黑时,我去坡下的澡堂洗澡。看到前面那个身影,正是何艳。我一阵慌乱,心跳骤然加快,有些喘不过气来。我加快了脚步。她也带着脸盆毛巾等物,往坡下走。我看见她穿着拖鞋,心里略安,总是追得上的。
我离她只有两步之遥了。我感到我们中间象有一个无形的弹簧,随着我的逼近,巨大的压力就压向胸腹部。我忍受着,东张西望地转移注意力。心里在想,这就是所谓的激动吧。
几乎快要挨到她了,我鼓起勇气喊了一声:“小何。”她迟疑了一会儿,还是将头转了过来。
我做了一下自我介绍,然后我们并肩走着,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。我们应该算老乡,都生长于一百公里外的长江中游的那座城市,父母和亲人也都在那里。到了澡堂门口,她拍了拍乱跑挡道的一个小孩子的肩,“真调皮。”然后递过两角钱给女澡堂的管理员,“五分钱算到下次吧。”就进去了。我则到男澡堂这边,掏出一元五角,买了十张票。
随后两天没有见到何艳。我们的英语培训班进行了一次测验,我是第一名。几个女生嘻皮笑脸地缠着我问问题,半真半假地让我在以后的测验中给她们提供方便。不知她们从哪里听说,英语考试的成绩与将来分配的工作岗位有关。我见第一排还有个空位,就换到那里去坐了。同桌就是那天给我吃麻糖的小杨,文静秀气,戴一副金边眼镜,象位女学究。
又过了两天,还是没有看到何艳。心里充满了疑惑和不安。这期间厂里有一次盛大的文艺演出,是为了纪念二十周年厂庆。领略了比较高层次的歌舞表演。看得我是目不转睛,喉咙冒烟。我感到有一种欲望,无以名之,姑且称为“对美的渴求”吧,烧得你坐立不安,可你不知道怎样满足。你也许想变成气体,变成液体,消失你自己,把自己和美熔为一体。可这又不可能。也许你会努力追求,占有,可你还是会发现:“我的热情被你耗尽,可你依然是你。”
下了大雪,滴水成冰。小杨手上有伤,是踩着冰摔了一跤。她可怜巴巴地对我们说:“这下子我相信有人摔一跤就摔死了。”老师表扬了她,说每次来教室都干干净净,以为我们是轮流值日,后来才注意到其实一直是杨玲一个人在打扫。小杨红着脸低下头去。
这天我又看到了何艳。我估计前几天她可能是回父母那里了。晚上我去敲她的门。没有人。大概是上班去了。
雨雪交加,风如刀割。我的四肢被冻得冰凉,头脑里却烧着火。我顶着风雪疾走,忽头上蓝光一闪,随后却是一片寂静。我吃了一惊:这是要地震,还是我精神错乱了?
我在电话班所在的厂生产调度楼门口转来转去。走近一些,又退后一些。好象听到了她的声音,却不知道在哪一间房。她既然在说话,那房里就不只一个人。就算推门进去正看见她,我该说什么呢?说有事找你,出来谈谈?还是说没有什么事,只是走到这里,顺便参观一下?这么恶劣的天气,脸冻得通红,牙齿在打颤。这是顺便参观吗?
想到那些给自己打气的方法,比如把人生看成一场戏,把际遇因缘看成一场梦,把他人看成心造的幻影或者小生物。自己这么一个唯一真实伟大的生灵,来扮演一次,来屈尊一次,有什么可怕的?
可你就是骗不了你自己。你发现你根本做不了自己的主。你不想脸红,偏要脸红;不想结巴,偏要结巴;想神色自若潇洒大方,偏要窘态十足欲盖弥彰。
我在楼口进进出出。冰地上是我茫然无绪的脚印。十米外有一只无家的狗,呆呆地看我,也不怕冷,喝着那滩冰水。
我只好往回走。路上见哆哆嗦嗦去上夜班的工人。这种天气连车也骑不成。他们也一样和我在冰天风地里煎熬。
回到寝室里,日光灯不时一闪,象要停电。我站在窗前,听外面鬼哭狼嚎的风声。日光灯又一暗,外面是一道黄绿色的光闪了一下。以为电停了,没想到一秒钟后又亮了。我觉得很恐怖,不知道我是不是在人间。一切都是非理性的。我忽然明白,最大的恐惧是对未知的恐惧。
又过了一天,天晴了。我坐在门口,前面是耀眼温暖的太阳,下面是冰。冰冻有一厘米厚。一些零星的小冰块停在窗台上,奇形怪状的。在一块大一点的冰砖上,我刻下她的名字。从某个角度看,笔划亮晶晶的,但慢慢就模糊了。
下午我注意到何艳一个人在寝室。我就去敲门。才敲两下门就开了。“进来吧。有事吗?”我支吾着,语无伦次。她却很大方地招呼我坐,告诉我桌上有报纸。又说很报歉,午睡才起床,被子都没有叠。我忙说没关系的。
她转过身,继续切萝卜,说是晚上上班带去当宵夜的。然后我就坐了一个多小时。彼此问长问短。这期间她一直侧面站着,有时也正面相对。我一直坐着,翘着二郎腿,双手箍在膝盖处。
我们聊了关于家庭,学习,工作等方面的事情。她提到她有一个双胞胎姐姐。她父亲在她们不到六岁时就把她们送进学校。当时学校对年龄管得比较严格。父亲对她们说:“要是老师赶你们走,你们就大声地哭,赖在那里不走。”她复述这话时,还翘了一下嘴唇,那种小儿女神态真让人心动。
我说注意到她总是独来独往。她说是呀,我喜欢清静。隔壁左右叫什么我都不知道。没事的时候我就呆在屋里看看书听听歌曲磁带什么的。
我试探地问她,有了男朋友吧。她踌躇了一下,说她想调到一百公里外的父母身边。不知这意味着是有男朋友在那边,还是调回去再找。
她拿了英语的自修大专文凭,还说想跟我们一起听课。我说“好呀”,鼓励她去听,她又说好象不太合适。
我回到自己的寝室,心情很舒畅。又有些兴奋。回头望去,我注意到何艳门口晾着一双棕红色的胶鞋,如一对可爱的松鼠。我开始设想,把一封信放在胶鞋里,她会有什么反应?我甚至想到了这封信的一个很好的开头:“我知道你去意彷徨。”可后面怎么继续下去呢?
这时培训班的杨玲戴着随身听的耳机,怯生生地过来问我几个英语方面的问题。课上她学得很认真,但由于从小在农村长大,基础很差,所以感觉很吃力。我耐心地指导了她。她说希望以后我能对她多指点指点。我说没问题。她高兴地去了。
星期天我去买了一双新鞋子。倍加珍惜地走路。我去了电话班。在总机室外敲门。何艳打开门,见是我,略有些吃惊。
她再三让我坐,说可以看看桌上的报纸。我则说想参观一下,就到程控机房看了看。
我转出来正想跟她聊聊,一个电话打进来,是内线,她说:“这样吧,你打到333,我跟你解释。”说罢就挂了,起身去机房接听。
这个过程很长。其间几次她过来接转这边的外线电话,然后又去机房接着说。她还对我说了一两句,什么某师傅每天这个时候都要过来玩玩的,不知今天怎么没有来。还说其实按规章制度,是不允许上班时串门的。
那边的电话打完了。她回来一言不发地记帐。给刚才那个长途记了四分钟。
这时一个陌生的小伙子推门进来。看着我说:“稀客。”我就问他哪个单位。他说是本厂。“具体呢?”“厂办”。她让他坐,他说:“对我也这么客气?”
后来听到他对她说:“你给你妈写封信。不写的话我写。”就此发生了一些争执。他们都去了门口,小声嘀咕。何艳还不时地回头看一下指示板,黄灯闪表示有外线进来。
过了一会儿,他转身往门外走。又折回,一句话不说。不久就听见他说:“他不走我也不走。”我无法确定他在说谁。他们两人都默默无语地相对而立,在小隔间外的玻璃门后。
我注意到我刚来时,她显得比较恬静,因暖气的缘故,脸红扑扑的,很好看。后来一急躁,变显得破坏了原有的和谐的美。
我好久没有看报纸了。我仔细地翻阅了她刚才拿过来的一叠报刊,有本地的日报,健康文摘,工人日报,中国建材等。
看完了报纸,我站着身,“你们这里报纸真不少。知道了好多新闻。”她说:“是吗?”我说:“不打扰了。我该走了。”他说“不再坐会儿?”“不了。”
到了外面。月亮很亮,尽管才是新月。我一边走一边想,不禁含着辛酸地笑了起来。
第二天下午,一时兴之所至,我爬到了附近的矿山顶上。这是这座城市的最高海拔。整个市区尽收眼底,只可惜被灰雾所笼罩。忽然想到以前看过的一篇文章,恩格斯二十岁时因失恋而登阿尔卑斯山。
在某岩层上有一台废弃的破碎机。旁边堆着尚未破碎完的石块。机器大体完整,只是锈得一塌糊涂。我想考证出机器的年代,未能如愿。整个现场让人有遗址的感觉。
玩得很尽兴。晚上去洗澡。出来时见到何艳和厂办秘书如树缠藤般地从广场走过。
杨玲又到寝室来问英语问题。她还提到她的家庭。他们住在北方一座大城市里。父亲是警察学校副校长,母亲是商场的柜台组长。她上高中时才到他们身边。他们对有知识的青年特别欣赏。她还有个读小学的妹妹。
休息日我带着刚发的工资上了街。买了一件羽绒衣和一条西裤。晚上是我们单位的包场舞会,庆祝新线的开工。舞厅里很多人,有的大人还带着小孩子来受熏陶。烟雾呛人。有的人竟还穿着工作服。不过,如果我不是上午上街买了衣服,恐怕也会穿工作服。
人们开始跳起来。一对对轻盈和谐。我眼巴巴地欣赏着。转眼一个多小时过去了。人们一曲曲地尽情陶醉。党委书记搂着团支书。宣传部的人跟踪摄影。这时我才明白,进来时看到的白光一闪是怎么一回事了。我差点笑出声来。我们科四十多岁的王科长也上台一展歌喉。
这时我坐到了杨玲身边。她看到了我,有些惊喜。“是你呀!”“是呀。”我凑近她耳边说。
我们随便扯了一些闲话,又一起走了几只曲子。尽管我踩不到节拍,她也没有显出嫌弃之意。
后来我们没有能坐在一块儿。快散场时,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出去,我还是呆呆地坐在沙发上。她也和旁边的人一起起身。走到我前面时,她迟疑了一下,又坐了下来,坐在我前面的沙发上。我说:“今天的气氛还不错。”她说:“比不上电厂。我姨妈他们在电厂,我去玩过。”
舞厅里的人所剩无几了。我们这才起身走出舞厅,走下楼梯。我有意走得慢些,与前面的同事们拉开距离。心跳加快了,我细细地品味话语堵在喉咙的感觉。是时候了,我必须把这句话说出来。这是我今晚唯一的目的。
“杨玲。”“哦?”“想问你一个问题。”
“你说吧。”
“May I be your friend”
“哎呀,你知道我听力不行的。”
“May, I , be , your ,friend”
“FRIEND,FRIEND是什么呀?”她的神态不象是装傻,而且显得比我还紧张。我忍住了泛起来的无聊感觉,沉默了一会儿,口齿清楚地告诉她:“朋友。”
“哦。”她又不说话了。
走了五步,她才说:“同事嘛,当然都是朋友的。”
这是一个很标准也很乏味的回答。我再没有说什么,只是沉湎在自己的思绪里。我那句有些可笑的问话,也许会让我铭刻在心,永生难忘。也许就象它看上去的那样,轻飘飘地,已经被温柔的晚风吹散。
这篇回忆性质的文章写到这里,感觉无法写下去了。于是我上网消遣。在打开了网上的一个很著名的搜索引擎后,我以“何艳”为关键词搜索了一下。有许多项结果,其中一项让我眼睛一亮。这是某区旅游局,网站联系人是何艳。当初隐约听到她要调到这个局去。我就往上面留的电子信箱里发了一封EMAIL,只有一句话:“你是当年在XX厂电话班工作的何艳吗?”
何艳是何时调离的我不太清楚。估计是在我和杨玲热恋期间。因为和杨玲确定了恋爱关系后,我去了外地培训,那时候程控电话还没有普及,杨玲给我打电话时还告诉我,是找厂电话班的何艳帮忙,打电话可以不交钱。而我的一年培训结束后,回到厂里,就再也没有看到她的身影了。好象当时惆怅过一阵子,可是正在和杨玲热火朝天地恋爱,后来又结婚生子,也就丢开了。
谈恋爱是人们常说的系统工程。这时候你会感觉自己的大脑不够用。许多种情绪许多个问题,让人应接不暇。
的确,我和杨玲是通过英语学习认识的,但基本确定了恋爱关系后,她还是纠缠于英语学习,就让人觉得很难以接受。好象是把爱情用来做为交易,交换一位英语家教。同时也把我置于嘴里总念叨着“要想学得会,就跟师傅睡”之类粗俗下流的人物的境地。
我还记得那样一幕,晚上我们嫌寝室里人来人往过于嘈杂,便一起来到我的办公室里背单词。忽然停了电。正好我抽屉里有两根蜡烛,是我以前在办公室独自看书时为应付频繁停电而置下的。
我们点亮了它们。烛光下她的面庞别有韵味。环境也是分外的悠静。这是一幢七十年代建的老办公大楼,苏式风格。前后左右被密密的树林和花圃包围。整座大楼除了我们空无一人。门窗紧闭。只是在最里面的一个房间里,有我们两个青年男女,围绕着美丽安详的烛光。
我开始心不在焉了,手也不规矩起来,先放在她的椅子背上,然后一点点搭上了她。她似乎没有察觉,或装做没有察觉,仍然在大声地朗读背诵,还不时地问我一些问题。我的浅层意识在倾听她的发音并给以指导,深层的意识却在试探着缩小我们物理和心理上的距离。我的手碰到了她的发梢,肩膀,手,膝盖。她没有退缩,只是掠过一阵局促。一阵阵的冲动在我体内拍打冲刷。
我凑近她纠正她的发音。我们离得如此之近,简直是口对口了。我鼓足勇气,干脆利落地把自己的嘴唇封上了她还在念着外语单词的嘴唇。
其实我本不想这样的,因为那几天天气干燥,我的嘴唇干裂了。但是到了这一步,做下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她稍稍摆了一下脸,还是让我吻上了。当时她的眉眼之间有很异样的表情。鼻息也急促起来。
吻完了,她一言不发,皱着眉,撅着嘴,象要哭似的。
我感叹到:“初吻是会让人记一辈子的。”
她说:“你还是继续考我单词吧。”
我就让她用英语把周围的一切说出来。她说了桌子椅子房子牛奶蜡烛等等。我说最关键的一项你漏了,affection,情感。
说罢我又想吻她。她挡开了。她说:“我是有男朋友的。”
我心头涌起一阵不快。我知道她指的是她母校的一位男老师。当初我没有认识杨玲时,还曾经传递过他给她写的信。后来她向我解释过,是快毕业时那个男老师追她。但她犹豫一阵子后委婉拒绝了。最近他也再没有来信了。但她今天居然又这么说。我追问她:“你是不是欠他什么?”她说:“什么也不欠。他给我买的东西我都退给他了。可我还是忘不了他。他对我很好。”
我也故意刺激她:“前天我们碰到王科长,他说到时候要喝我们的喜酒,你也笑嘻嘻地默许了。现在又说我不是你的男朋友了?搞了半天,原来是利用我来辅导你英语啊。”
她也反唇相讥:“利用你又怎么样?你又是什么正人君子?名义是辅导英语,还不是借机玩弄女性?”
我气急败坏又无话可说。就象被人泼了一盆脏水,很想声称自己本来冰清玉洁却做声不得。
“好了好了。别生气。其实说心里话,你们两个都不错。要是能同时有两个男朋友该多好呀。”
“哼,做你的美梦吧。”我冷言冷语。
“你不是说要送一件圣诞礼物给我吗?”她又想到了这件事。
“其实我原来是把我的初吻作为最珍贵的礼物的。没有想到你根本不在乎。”
“谁说我不在乎啦?不过实实在在的东西我更喜欢呀。你那天不是说要送我一本很好看的书吗?”
我怏怏地打开我办公桌的最边上一个抽屉,取出一本装帧精美的书和一大袋奶粉。书是英文版的《GONE WITH THE WIND》(《飘》)。我上个月托我在国外留学的同学寄来的。
她很高兴地接受了它们。她还说相信有一天她能流畅地阅读这本英文书。告辞的时候,她还叮嘱我吃点维生素,对嘴唇的干裂有疗效。
写到这里我起身去书架边,在角落里找到了这本书。封面已经旧了,里面的书页还崭新如初。在扉页的原书题辞“to J.R.M”下面,是我的试图工整洒脱却仍显稚嫩呆板的中文字迹,已经有些褪色:
“给我的玲:
等北斗把盛满了的东西倒出来,我就乘机放进去我的故事,在那里等你的眼神。我希望,我也能读你,仔细读你。”
我现在还模糊地记得,这一段话是从一本《港台散文选》中抄录下来的。
(待续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-作者:三不知
--发布时间:2004-1-14 9:06:00
--
其实那一天还发生了另一件事。杨玲在我们接吻后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:“你会爱一个比你大两岁的姑娘吗?”我真觉得莫名其妙。现有一个小两岁的在谈着,怎么又去爱一个大两岁的?再追问时她又强做笑脸,“随便问的,开玩笑的。”
回寝室后我警觉起来。心情变得沉重。我想起一次借她的指甲刀,发现上面的生肖图案与她的年龄不对,当时也没有在意。现在一想,正是大我两岁的生肖呀。可我就是无法从外表上分辨一个姑娘是二十岁还是二十四岁。怎么会这样?她到底有什么不堪回首的过去?抹去的四年时间她在干什么?又想到她父母的年龄。她父母怎么不到二十岁就生了她?想来想去不得而知。心里象压了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。在床上翻来覆去,深夜两点钟时,我觉得我想通了:无论她有过什么样的坎坷,不幸,挫折,伤心往事,不堪回首的记忆,我的情感依旧,甚至更强,更坚定,更不屈不挠,更体贴,更关怀。想通以后,我才安然入睡。
第二天我们没有机会见面。我和本厂其他几十名代表被通知参加市里的一个选举大会。会场庄严肃穆,气氛热烈。但我只是安静地坐着,沉静在自己的思维中。我想起以前许多一笑置之的说法,例如缘份,例如生命的另一半,例如爱情使人成熟,例如弱水三千取一瓢饮,例如如鱼饮水冷暖自知。在人为的喧嚣欢快中,我独自向隅潸然泪下。
后来当我有机会向她讲述我心灵的挣扎和思想的历程时,她却不屑地笑了,“你把我想象成什么了?我有什么不堪回首的过去?说我是什么蒙尘的宝玉?好象说我不清白似的。你真是小说看多了。”
直到后来,我们已经多次在床上进行那种恋人之间的擦边球游戏,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,她才在我的追问下陆续解开了她的年龄和家庭之谜。一旦弄清楚了,也就索然无味,甚至我都没有兴趣把它再写下来。说到底,是在一个不公正比较严重的社会里,一个农民家庭为了孩子有个学上,有个饭碗,利用城里亲戚的关系上下打点,终于获得有限成功的故事。确实存在欺骗作假,但也谈不上大奸大恶,算不上可歌可泣。
在耐心等待几天后,我收到了何艳回复的EMAIL。上面也只有一句话:“GONEWITHRAIN,你又是谁呢?”(GONEWITHRAIN是我电子邮箱的用户名。)
我很高兴,掺杂了一些激动,也有一点果然不出所料的得意。这样,和何艳不通音信近十年后,我们又通过EMAIL开始了频繁的交流。
五一长假,杨玲要加班,我带孩子去看望故乡的父母亲。他们在帮我的妹妹、妹夫带孩子。这也是何艳工作和生活的城市。第二天,我打了何艳的手机,并问她可不可以见她。她爽快地同意了。我们约在肯德基快餐店前的城市广场见面。
我跟孩子说我有事要出去一趟,让他就呆在家里,跟他的表弟一块玩。他点了点头。我迅速地离开,不忍心看他那落落寡欢的眼神。
杨玲确实是在加班。但是如果要一块来也不是什么难事,换个班就行了。但她自从因为种种家庭琐事和我家里人吵翻以后,就再也不肯来了。
是的,在家庭生活中我获得了宝贵的安定和舒适,但这绝不是没有代价的。甚至我觉得我在婚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,一个以前的我一定会嗤之以鼻的一个人。以下是我的一段笔记:
“《悲惨世界》观后感。
“制造无边黑暗的是人心,制造无限光明的也是人心。今夜当我看《悲惨世界》的VCD时,心灵随之波动。知道了有许多作品是模仿它的。所谓煽情一类吧。又名浪漫主义。
“心灵尚未平静,看看钟,已到了该喊她起床上夜班的时候。我喊了她,她半梦半醒的,发出呓语:"什么事呀!"过了一会儿她才清醒过来,想起了要上班的事。知道时间还充裕后,并不是促地起身穿衣服。我无聊地站着,看着她那瘦小的半睡半醒的身躯。在微光中只有一个轮廓。没有开大灯,怕影响熟睡中的孩子。忽然想到:这难道不也是一个悲惨世界吗。
“你如果老老实实地上过夜班,你一定会觉得无法忍受。但如果你无法逃避,你也就只好忍受,并且也就这么一直忍受着。但这仍然还是一种痛苦,不会稀释,不会异化,也不会升华。
“我们几个小时前才发生了柴米夫妻常有的争吵,彼此都用了很恶毒的字眼,心里充满了很恶毒的想象。但此刻,这个瘦小的身躯,这个忙里忙外却不得一夕安寝的身躯,这个在微光中、在严冬里穿裹着工作服棉袄的身躯,却让人如此的怜爱难舍。”
对,就是忍耐,就是妥协,就是相濡以沫,就是互相伤害又互相抚慰。我们过着在外人和自己看来都淡然无味的家庭生活。
到了城市广场,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。我先去商厦转一转,准备给何艳买点礼物。人很多,毛毛雨也停了,温度上升得很快。早上我穿了一件毛衣,现在觉得实在受不了了。但脱了毛衣,里面只有一件秋衣,而且还汗湿了,这个样子怎么好见她呢?中生智,迅速去衬衣柜台买了一件五折的中国名牌衬衣。买了之后,又急忙走进男洗手间,把装衬衣的精美纸盒丢进垃圾桶,大塑料袋用来装脱下的毛衣,然后把衬衣上的十几根大头针一一拈除,背面垫的纸板和领内的塑料硬衬也扔进垃圾箱,然后把这件崭新的名牌衬衣穿在我汗湿
今天的内容先分享到这里了,读完本文《﹝擦边球什么意思﹞擦边球什么意思生肖》之后,是否是您想找的答案呢?想要了解更多,敬请关注www.zuqiumeng.cn,您的关注是给小编最大的鼓励。
本文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立场,转载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zuqiumeng.cn/wenda/1122339.html